清明档电影|流量演员扎堆特殊群体角色,是救赎还是消费?
今年清明档,电影市场呈现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。在《向阳・花》中,赵丽颖化身罪犯母亲高月香,为了给失聪女儿筹集 20 万人工耳蜗的费用,不惜铤而走险;而在《不说话的爱》里,张艺兴挑战聋人父亲小马一角,为留住女儿抚养权,不慎误入犯罪深渊。自带流量的青年演员纷纷投身于特殊群体角色的塑造,这一趋势并非偶然,去年便已初露端倪。易烊千玺在《小小的我》里成功塑造脑瘫青年刘春和;佟丽娅与黄明昊在《假如,我是这世上最爱你的人》中,分别刻画了断臂女性和听障少年;即将到来的五一档,张婧仪为了在《独一无二》中诠释好听障家庭中唯一听人女儿的角色,特意学习了手语。
一时间,青年演员们纷纷卸下华丽精致的戏服,画上质朴粗糙的妆容,努力学习小众的手语,全身心地投入到现实主义题材的影视创作中。然而,在这场看似立意崇高的创作浪潮背后,诸多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:这究竟是真心实意地关怀特殊人群,还是仅仅为了制造宣传噱头?流量演员出演特殊人群,对电影票房的提升以及自身的转型发展究竟有多大作用?当 “流量演员 + 苦难题材” 成为现实题材电影的创作定式,电影行业又会迎来怎样的影响?
流量能转化为票房吗?
在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中,不乏聚焦特殊群体或底层人民的现实主义佳作。像薛晓路执导的《海洋天堂》,深刻展现了孤独症患者面临的生活困境;娄烨镜头下的《推拿》,生动描绘了盲人世界的独特景象。这些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视角,真实地呈现了特殊群体的生存境遇。然而,文艺属性与沉重题材的双重特性,使得它们在票房方面始终难以取得重大突破。
近年来,影视行业试图探索一种新的破局模式 ——“流量演员饰演特殊群体”,期望通过明星效应与社会议题的有机结合,为现实题材电影带来更为可观的商业价值。2020 年,易烊千玺和刘浩存在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中,生动塑造了性格迥异的癌症患者形象,展现了这一特殊群体面对人生挑战时的不同态度。该片最终斩获 14.32 亿的票房佳绩,似乎为 “流量演员 + 苦难题材” 的创作路径提供了成功范例。
此后,这种创作模式逐渐被广泛复制。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,影视行业格局发生巨大变化,自带流量的青年演员愈发频繁地出现在现实题材电影中。易烊千玺、赵丽颖、张艺兴等众多明星纷纷在电影里挑战特殊群体角色,他们所饰演的角色,有的身患重症,有的身体残障,还有的身处社会底层,需要照顾残障家人。对于演员而言,这类角色往往具有更广阔的表演空间;对于电影来说,流量明星的加盟在一定程度上也提升了其商业价值。
但随着行业环境的持续变化,残酷的市场数据无情地打破了流量带来的票房幻想。今年清明档,凭借赵丽颖和张艺兴的影响力,以及影片题材本身的话题性,《向阳・花》和《不说话的爱》在映前收获了极高的热度,“想看人数” 和预售成绩均名列前茅。上映首日,两部影片也获得了排片上的明显倾斜,《向阳・花》排片占比达 25%,《不说话的爱》排片占比为 20.5%,分列清明档前两位。
然而,令人遗憾的是,两部影片都未能将映前的高热度转化为实际票房。从首日上座率来看,《向阳・花》仅为 4.8%,《不说话的爱》为 4.7%,与《我的世界大电影》(10.3%)和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(11.1%)相比,差距十分明显。最终,游戏改编电影《我的世界大电影》以黑马之姿夺得清明档票房冠军,《向阳・花》位居第二,预售成绩第一的《不说话的爱》甚至不敌已经上映两个多月的《哪吒 2》。截至目前,《向阳・花》和《不说话的爱》的预测总票房与映前相比,已大幅下跌。
问题究竟出在哪里?不可否认,电影市场观众流失是一个重要因素,但流量经济在电影市场再次失灵也是不争的事实。此前,《小小的我》上映初期同样备受关注,易烊千玺作为极具票房号召力的青年演员,其每一次亮相都备受瞩目。然而,该片最终票房成绩未达预期,7.65 亿的票房在易烊千玺主演的电影中并不突出。《我们一起摇太阳》票房表现更是不佳,甚至一度撤出春节档,二轮上映后累计票房仅 2.74 亿。坐拥暑期档优势的《假如,我是这世上最爱你的人》,由佟丽娅和黄明昊主演,票房也仅仅刚过 1500 万。
现实题材电影近年来虽然越来越受到行业推崇,但流量明星的加入并未如预期般为电影票房带来显著的附加价值。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,当流量明星涉足弱势群体题材时,电影的粉丝属性变得极为突出。这种现象反映在电影市场上,就是电影映前预售成绩往往十分出色,但由于口碑不佳,影片的长尾效应有限,映后票房曲线难以持续上扬。反映在电影创作上,流量明星的加盟常常导致创作重心发生偏移。重疾和残障等设定被滥用,成为推动剧情发展的简单手段,演员的表演也更多地流于表面,追求视觉上的奇观效果,而弱势群体的真实困境却被简化为一个个符号,得不到深入展现。当流量演员主演的聚焦底层群众的电影不断涌现,我们不得不深思:这场立意看似崇高的创作实验,究竟是真心关怀特殊人群,还是仅仅为了制造噱头?
关怀社会还是制造噱头?
《向阳・花》聚焦刑满释放女性重返社会所面临的困境;《不说话的爱》以聋人家庭的亲情羁绊为主线;《小小的我》深入探索脑瘫患者的生活世界;《我们一起摇太阳》讲述了两个重症年轻人之间 “生命接力” 的约定。不可否认,这些电影将目光投向被社会忽视的特殊人群,试图唤起观众对弱势群体的理解与同情,选题本身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。
在宣发过程中,《不说话的爱》邀请听障群体参与观影交流活动,并推出助听字幕版;《小小的我》在影片上映后发起 “苔花公约”,积极推动企业为残疾人提供就业岗位。这些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特殊群体的关怀,促使观众开始关注少数群体的生存状况,也为电影赋予了更为深刻的社会价值。
然而,问题也随之而来。当流量演员在影片中成为特殊人群的代表,其主角光环被过度放大时,不仅可能压缩配角的发挥空间,更会弱化电影所关注的社会议题。例如,在《不说话的爱》中,黄尧饰演的木木妈妈经济条件优越;在《小小的我》里,周雨彤饰演的雅雅阳光健康。她们作为男主生活中极为亲近的人,在剧情发展中却缺乏完整的人物故事线,在男主的成长蜕变过程中也几乎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,使得这两部电影几乎成为了张艺兴和易烊千玺的个人表演。
从故事层面来看,由于主角光环的过度影响,真正用于展现电影核心议题的篇幅被严重压缩。在《向阳・花》中,为失聪女儿筹钱购买人工耳蜗是高月香的核心诉求,但在整部影片中,失聪女儿的形象单薄如纸片,母女之间同框的场景不仅次数稀少,而且十分仓促,使得这条关键情节线显得极不完整。
在 “流量演员 + 苦难题材” 的创作模式下,电影的叙事方式逐渐向以流量演员为核心偏移,宣传方式亦是如此。在社交平台上,赵丽颖、张艺兴学习手语的片段被反复炒作,成为宣扬演员 “敬业” 的有力证据;易烊千玺为塑造脑瘫形象所展现的歪嘴、抽搐等外在表演,也成为网络热议的焦点。这些片段被单独剪辑出来,在网络上广泛传播。片方深知,相比严肃的社会议题,放大演员的所谓 “颠覆演技” 更容易制造传播热点,吸引大量流量。
这种营销策略所带来的直接影响是,公众讨论的焦点大多集中在流量演员身上,而电影原本想要传达的社会议题却被冷落一旁。电影逐渐从 “为特殊群体发声” 演变为 “为流量演员打造光环”,特殊群体在这一过程中反而成为了陪衬。
这种矛盾在舆论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。在《向阳・花》的路演活动中,一位来自普通家庭的听障儿童母亲在观影后,深受触动,她上台向赵丽颖分享自己与影片中高月香相似的经历,表达了对电影的强烈共鸣。然而,这一事件在网络上发酵后,登上热搜的却是赵丽颖听故事时落泪的画面。特殊群体的真实声音,在喧嚣的流量狂欢中再次被淹没,无人倾听。
底层叙事成了流量转型的跳板?
流量演员大量涌入现实题材电影,出演特殊人群角色,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身转型的考虑。对于演员来说,摆脱单一的形象标签,尝试多元化的角色塑造,不仅有助于提升自身演技,冲击各类奖项,更有望实现事业上的新突破。
以赵丽颖为例,从《第二十条》中戏份有限的配角,到《向阳・花》中的绝对女主,她在转型之路上迈出了坚实而大胆的步伐。在这两部作品中,郝秀萍和高月香这两个角色虽然处于不同情境,但都深陷社会边缘,为了孩子不惜与命运顽强抗争,具有一定的相似性。随着对角色理解的不断深入,赵丽颖手语越打越熟练,通过对这两个 “失语者” 角色的精彩演绎,在现实题材领域逐渐站稳脚跟。凭借在《第二十条》中的出色表现,她荣获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,这无疑是对她转型努力的高度认可,也证明她在转型道路上找到了正确方向。
在演艺圈中,通过出演特殊群体角色成功实现转型,最终成为影帝影后的例子并不少见。吴慷仁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。曾经在偶像剧《下一站,幸福》中,他饰演苦恋梁慕橙的花拓也;而在电影《富都青年》中,他却摇身一变,成为以无声表演打动观众的哑巴阿邦。凭借在《富都青年》中的精湛演技,吴慷仁成功斩获中国台湾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。同样,钟雪莹在电影《看我今天怎么说》中饰演听障者,为了演好角色,她努力模仿正常人说话,其出色的表演不仅为她赢得了中国台湾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,还获得了今年中国香港金像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。
虽然不同电影奖项的评选标准存在一定差异,但对于表演类奖项而言,演员的表演技巧、对角色深度的挖掘以及情感的精准传达等,始终是重要的评审依据。相较于普通角色,特殊群体角色往往蕴含着更为强烈的情感冲突,同时演员在身体语言、表情等方面的表现也更容易形成视觉上的冲击力,从而为演员提供了更广阔的表演空间。基于此,流量演员扎堆出演特殊群体角色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去年,金鸡奖最佳女主角授予了《我们一起摇太阳》中的李庚希。评委会对她的评价是:“李庚希在影片中与角色融为一体,以纯粹有力、细腻真挚的表演,鲜活生动地刻画出凌敏的痛苦与坚韧、抗争与希冀。在微妙表情动作中传递情感变化,在泪水滑落间深挖角色内心,展现出一名青年演员在表演上的敏锐与成熟。” 从这段评语中,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评委对演员演技和角色塑造深度的重视。这种评奖倾向进一步强化了演员转型的内在逻辑:特殊群体角色所具备的情感烈度与身体奇观,能够有效提升演员的表演层次。对于演员而言,饰演特殊人群并非创作的终极目标,而更像是在攀登职业高峰过程中,手中的一把得力工具。
“流量演员 + 特殊群体” 成为电影创作的一种模式,本身并无不妥。但创作者们应当深刻反思:当流量演员借助特殊角色在颁奖季收获满满时,电影本身究竟向观众传递了哪些具有深刻内涵的信息?演员与电影之间,本应是相互成就的关系,演员为电影增添光彩,电影助力演员成长,实现双赢才是理想的良性发展方向。然而,当下的现实却让我们不得不思考,这种创作模式是否已经偏离了初衷,沦为一种表面热闹却缺乏深度的形式?我们期待看到的,是真正能够深入挖掘特殊群体内心世界、展现其真实困境,同时又能让演员充分发挥演技的优秀作品,而不是仅仅将特殊群体作为吸引眼球、助力演员转型的工具。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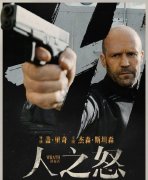 李宛妲带你解锁CCTV6一周佳本周《光影星播客》嘉宾李宛妲为我们推荐了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即将播出的好看影片,让我们跟随她的介绍一起看一
李宛妲带你解锁CCTV6一周佳本周《光影星播客》嘉宾李宛妲为我们推荐了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即将播出的好看影片,让我们跟随她的介绍一起看一 -
 台式青春席卷!2025年度必当彩带与心跳同频共振,青春里最有病的喜欢终于有了姓名!由许富翔执导、赖宇同监制,詹怀云、江齐、刘修甫、黄
台式青春席卷!2025年度必当彩带与心跳同频共振,青春里最有病的喜欢终于有了姓名!由许富翔执导、赖宇同监制,詹怀云、江齐、刘修甫、黄 -
 外媒曝罗伯特·帕丁森有望Deadline报道:《沙丘3》相中了罗伯特帕丁森出演,目前还未正式给出offer,但希望他演的会是一个重要角色。THR称该片
外媒曝罗伯特·帕丁森有望Deadline报道:《沙丘3》相中了罗伯特帕丁森出演,目前还未正式给出offer,但希望他演的会是一个重要角色。THR称该片 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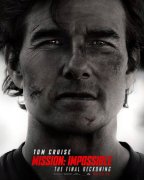 《碟中谍8:最终清算》将《碟中谍8:最终清算》入围第78届#戛纳电影节#非竞赛展映单元,将于戛纳当地时间5月14日举行全球首映式。 主演兼
《碟中谍8:最终清算》将《碟中谍8:最终清算》入围第78届#戛纳电影节#非竞赛展映单元,将于戛纳当地时间5月14日举行全球首映式。 主演兼 -
 电影《钻石照耀钟鼓楼》《钻石照耀钟鼓楼》以幽默诙谐的风格和浓郁的 新时代京味儿,讲述了一个发生在胡同里的生活流故事。赵小鹿(陈芋
电影《钻石照耀钟鼓楼》《钻石照耀钟鼓楼》以幽默诙谐的风格和浓郁的 新时代京味儿,讲述了一个发生在胡同里的生活流故事。赵小鹿(陈芋 -
 《猎金游戏》发布“一入邱礼涛编剧并执导,刘德华、欧豪领衔主演,倪妮特邀演出,黄奕、郑则仕、蒋梦婕刘以豪等特别演出的电影《猎金
《猎金游戏》发布“一入邱礼涛编剧并执导,刘德华、欧豪领衔主演,倪妮特邀演出,黄奕、郑则仕、蒋梦婕刘以豪等特别演出的电影《猎金

